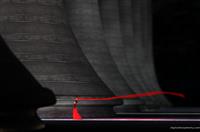陵川县南召文庙及戏曲碑刻考述
《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2017年04期
段飞翔 曹飞
内容提要∶文庙修建、祭祀必定要在官方的管控之下进行,这与其他庙宇相比存在明显不同。但是田野考察中陵川南召文庙的发现让人产生诸多疑惑,其建筑格局明显不合文庙规制,甚至庙内还建有戏楼供祭祀献戏之用,这与文庙祭祀必用“雅乐”的礼制逻然不同。本文将以南召文庙个案考述切入研究,以期能揭示现象背后的内因,并为民间剧场史、演出史研究提供一些案例。
一、庙貌概况与建筑形制
陵川县位于晋东南,北接壶关,西邻高平,南靠泽州,东临河南省。汉属泫氏县,隋开皇十六年(596),析高平置陵川县而至今。明初属平阳府,后至清隶属泽州府,今属晋城市。南召村距县城7公里,今属平城镇。村中遗存文庙一座。根据《陵川县南赵村为重修古庙记》碑文记载∶“自昔传遗文庙一座,创始未知。大明洪武二十二年岁次己巳揭盖,至今二百余年,庙貌颓岩,人心共愤。于万历十六年岁次戊子七月吉日兴工。”“可知,其创建年代应在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之前。笔者实地考察发现,文庙正殿建筑明显存有金元之风,殿内金柱等部分构件均为原物。根据正殿一般多为庙宇之中最先建立的客观事实,推知此文庙至迟在金元时期就已经开始兴建。此后,经过历代修缮最终形成现在的格局。文庙现存建筑有正殿、配殿、看楼、戏楼、耳房等。
南召文庙坐落于高岗之上,依山就势而建。从现状看,庙院为四合院落布局,最南端为山门舞楼。上层建戏楼,下层为文庙山门,其中明间较宽敞,次间相对狭窄。明间额题“德配天地”,东西额题“登圣域”、“启贤关”。戏楼两侧配耳房,上下各三间,带前廊,上层木柱,无斗拱。东西两侧建看楼,硬山顶,灰脊板瓦覆布。墀头砖雕瑞兽。面阔五楹,四架椽,通宽14.25米,进深3.5米。
正殿坐北朝南,悬山顶,灰脊筒瓦,脊饰吻兽。檐柱为方形抹角石柱,柱上施拍枋,上置斗拱,柱头四朵,四铺作,华拱、耍头均刻昂形,补间无斗拱。正殿面阔五楹,宽14.25米,进深六椽,6.78米。廊深2.74米。金柱间装六抹隔扇门。走马板上有四字额题,中间“圣协时中”,左右为“珠源流泗”、“祈户加帮”。殿内减柱造,仅用两根金柱承重。柱高2.5米,侧角、收刹明显,素平础。柱头栌斗承接顺梁,连接两金柱之内额在柱头之外出头形成较长的压跳。顺梁之上置栌斗承接泥道拱与华拱,华拱承托由后乳袱的一端形成压跳,并可见翼形小拱,后乳袱正压于四椽袱之下,四椽袱的另一端搭在廊柱之上,四椽袱之上设蜀柱,柱头置斗拱,斗拱两翼置散斗,承接替木,承于平樽之下,平梁两端穿入平樽与斗拱之间。平梁上施叉手、蜀柱、合沓、丁华抹颏拱,承托脊樽撑起屋顶。殿内原塑孔子及“十二哲”泥塑,可惜毁于“文革”。正殿石砌台阶,基高0.7米。台基之下为一平台,高0.65米,长9米,宽8.5米,可能为祭祀或看戏之用。
戏楼硬山顶,灰脊筒瓦覆顶,一面观。面阔三楹9.25米,其中明间3.75米,基高2.8米。戏楼檐下无斗拱,挑檐檩,置于五架梁之上。戏楼梁架为五檩四架椽。五架梁前出,梁头刻瓣,下枕大斗,之下为大、小额枋,雀替,均精心雕刻,且构图奇特,有“龙在两侧凤在中,凤捧炉鼎正当央”之势。檐柱四根,方形抹角石柱,柱高3.37米。戏楼用木隔断分开前后台,前台进深3.6米,后台进深1.4米。其中明间隔断向内缩进0.6米,此做法适当增大了明间的表演空间。隔扇多有木雕装饰,多具审美价值。戏楼及耳房山墙之上多处遗存舞台题记。
二、文庙出现戏楼考疑
文庙,是国家主持修建以祭祀孔子为主的礼制性庙宇。孔子作为儒学奠基人,他的思想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公元前478年,鲁哀公在陬邑以孔子旧宅立庙,当时的“庙屋三间”就是中国最早的孔庙。此后孔庙这一称谓历代多有变化。唐开元年间孔子被册封为“文宣王”时,孔庙改称文宣王庙。宋金元时又先后称作至圣文宣王庙、大成至圣文宣王庙。明代以后孔庙才多称“文庙”。文庙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载体与象征,加之历朝历代都有尊孔之实,其从家庙发展到国庙再到遍地开花,经历了一个繁荣发展的过程,至清末全国共建有孔庙1560多座。文庙作为政治、文化和教育三者融合的产物,在其建筑规模、祭祀贤儒和祭祀仪礼方面一直受到官方严格控制。从建筑规制来说,文庙作为极具代表的一类建筑群亦是如此,依州府而下全国各地文庙建筑组群都必须遵循一定规制。
从祭祀礼制来说,文庙祀奠主要是行礼,它是在音乐、歌唱、舞蹈的衬托下进行的。按照一般惯例,“文庙祭祀的是大成至圣文宣王,以颜回、曾参、子思、孟子之"四配",及冉耕、宰我等"十二哲"配享,庙宇跨院还有当县教谕或州学正、府教授的府邸这些相应的设施,整座庙宇是一纯粹读书人的世界,儒学圣地,祭祀活动也主要祭祀先秦大儒孔子,祭祀遵循古典的儒家礼法,有着很严格的祭祀体系,从来不许普通百姓参加,自始便与俗文化绝缘”。文庙祭祀历来都受官方重视,在祭祀过程中必重礼乐、雅乐的使用,而排斥和轻视俗乐,所以在文庙中通常建有演歌舞的露台而不建戏台。但是笔者在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却陆续发现了陵川县平城镇南召村文庙,平顺县青羊镇吾乐村文庙,黎城县西井镇南桑鲁村孔庙中有戏台的遗存。除此之外,还在邑廪生申时显撰于清嘉庆八年(1803)《重修文庙序》碑刻中发现了增修“歌楼”的记载乾隆五年重修为五间,又增歌楼三间。踵事增华,较前之人制更觉灿然可观矣。迄于今,历年久远,殿宇复至于倾圮,垣墉半就荒芜,耆老目观心伤,于嘉庆六年四月内,土木之功复兴焉。廊庑仍循旧规,歌楼增为五间,施其丹腹而晕飞耀彩,勤其朴质而鸟革争荣。
看到这样的客观现象之后,不免让笔者产生两点疑问∶其一,受到封建礼制的规范和限制,为何乡镇村落会有文庙遗存;其二,在文庙祭礼必用礼乐、雅乐的制度规范下为何会在庙内建有戏台。根据田野考察时看到的情况,笔者总结了这几处文庙普遍具有的特征。首先,从建筑形制和规模来看,三处文庙都比较简陋,并无万仞宫墙、棂星门、泮池、大成门等这些文庙标志性建筑;其次,从建筑格局来看,三处文庙内都在正殿对面建有戏楼;再次,从其所处区域来看,三处文庙无一例外都建于村落。综合分析这些特征之后,笔者认为此三处“文庙”并非正规意义上的文庙,它们可能只是乡村中培养学生的乡校、学馆。而这一猜测并非毫无根据,因为在封建时期上党地区民众多信仰儒学,设庙立馆祭祀孔子并进行文教活动的现象十分普遍,所以这样的庙宇被当地民众冠以文庙之名也符合情理。关于此,当地的金石志书中也多有相应记述∶
且夫乡曲之间立庙以祀至圣,稽诸曲礼未协也。余自下车以来,高邑数大镇遂在咸有,心甚讶之。爰是访诸父老,询之土人,金曰∶为明道先生讲学处。文庙之设,有自来矣。明道先生移令晋城,诸乡皆设校馆,暇则亲至,召父老与之语,又亲为儿童正句读,此乡之所以有庙也。
学之系乎人大矣。古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天子曰辟雍。诸侯曰叛宫,下逮乡、党、州、闾皆有学。凡入学、必释奠于先圣先师,此后世文庙所由起也。然必郡县学乃立庙,而乡则否。盖学宫有司春秋致祭,而乡校则有司所不至。生徒分合,靡有定处,亦无所事于庙也。惟宋程明道先生令晋城,以养民善俗为先,建设乡校百有余所,亲为童子正句读,教化大行。高平其邻邑也,遂亦相竟于与乡多立校焉。乡既有校,则必立主以祀先师。迄于后世,学徒衰散,而校之故址犹存,辄修而葺之,称为文庙。第其规制殊隘,故立于乡而不为僭也。
以上三则材料中所指的“文庙”均是因文化教育而建的乡校。众多此类“文庙”的存在一定程度上与北宋程颢出任晋城县令期间广泛推行教化政策所产生的影响有关。对此车文明先生认为“程子立学校、厚风化被地方史志以及后世名人屡屡提起,甚为自豪,已经积淀成为一种长久的集体记忆,成为当地一种强有力的文化象征"。南召、吾乐、南桑鲁三处村落中文庙的存在就是受此文化影响的外在体现。它们在地缘位置上都靠近古泽州一带,客观上均处在文化影响的有效辐射范围内,受明道先生曾在此地普建乡校的影响,后代于此地村落普建文庙的做法也就显得十分正常。基于这些考虑,南召文庙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属于当地民众修建的乡学、校馆一类,而非正规意义上的文庙。从第三则材料“盖学宫有司春秋致祭,而乡校则有司所不至”、“第其规制殊隘,故立于乡而不为僭也”的记述中,也可以为村落出现文庙并且还建有戏楼的现象提供一些启示。
但要深挖三处文庙建有戏楼的原因,还必须考虑其所处的时空环境。此三处文庙都位于太行山区,而太行山地处山西东南部,是山西省与河北、河南两省的交界岭。由于山多土瘠,交通不便,乡民生活历来都较贫困,然而敬神尚礼之风却蔚为大观。有赛社就必有酬神演出,这作为一种传统,贯穿于太行乡村的祭礼活动中。自宋以降,及至明清,遍布太行山区的神庙剧场亦可反映该区域戏曲演出曾经有过的繁盛。封建时代戏曲作为传播文化的重要艺术载体,其还具有教化和娱乐的属性。民众在观看戏曲演出的过程中不仅可以使身心得到娱乐,而且在轻松娱乐的氛围中亦可获得教益。基于戏曲的这些效用,民众在庙宇中进行祭祀奉神的过程中,戏曲就常作为民众敬献给神的贡品而在庙宇当中搬演。从实用性角度考虑,庙宇中的戏曲演出不仅可以在敬神、奉神的过程中表达民众的虔诚,而且于此过程中戏曲演出还可以用来娱神、娱人,进而达到一石二鸟之目的。在文庙中修建戏楼进行戏曲演出亦可达到同样的效果,民众何乐而不为呢。
当该区域庙宇内祭祀演剧发展成为一种常态时,戏楼作为固定承载戏剧演出的载体就顺其自然的出现在庙宇之中。戏楼作为“神庙中演剧场所的专设源于神庙祭祀时礼制所需,是祭祀仪式中为神灵敬献乐舞戏曲的专设场所,甚至成为一些神庙中必不可少的礼制配置”。可见戏楼能够出现于神庙当中并被民众普遍接纳,其最根本的原因是受民间礼乐观念影响所致。例如明嘉靖十五年(1536)《重修乐楼之记》所载∶“尝稽诸《易》曰∶先王以享帝立庙。又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故庙所以聚鬼神之精神,而乐所以和神人也,此前人立庙祀神之由,乐楼所建之意也”①,自然的流露着当地民众对礼乐观念的接纳和重视;明弘治十四年(1501)《创建礼乐楼记》载∶“建礼乐楼三楹,栏护四傍,用主礼乐以事神”²,清楚明晰的表明了当地民众在奉神、祭神时不可无戏的主导思想。这些民间大众所述“戏楼”创建的原因和目的中,无不体现着民间礼乐观念对庙宇中创建戏楼的重要影响。
从三处文庙分布在村落这一特殊的空间地域环境来看,它们更靠近乡村民众的社会生活区域。在庙宇的创建和祭礼活动中更易受到民众礼乐观的影响。基于该区域民众对庙宇中创建戏楼和祭礼演戏的接受与重视,使得在三处文庙内建戏楼的特殊现象于民间礼乐观的影响下就变得合情合理。再加之当地戏曲的繁荣发展与民众对戏曲艺术的喜爱与接受,都在很大程度上为文庙与戏楼二者的结合提供了契机。
南召文庙作为当地文教中心曾一度受到各阶层的普遍重视。由图表可以清晰地看出,此次重修文庙捐资的主体是由三类人员组成∶第一类是在职与候补的文武官员,捐资人数达23人次,捐资库平银502两2钱;第二类是外地商铺34家,捐资金额72两;第三类是本土商铺20家,捐资金额总计19两20钱4千文。三类捐资人(铺)数与总人(铺)数之比分别为∶30%、44%、26%,由此可见,商铺无疑是参与群体最多的主体。从官员(在职与候补)、外地商铺、本地商铺捐资金额约为25∶3.6∶1的比例关系分析,官员(在职与候补)捐资数额所占总金额的数量最大。可知正是官僚阶层与商人阶层的鼎力支持才保证了此次南召文庙的重修能够顺利完成。
再从参与此次重修捐资官员的结构来看,他们多是在浙江各府县任职或可能赴浙江任职的文武官员,笔者在此对碑刻里涉及捐资官员的基本情况进行了梳理。
从这些官员的籍贯可以知道他们都非陵川县人,并且于光绪前后的《陵川县志》中也没有发现他们在当地做官的记载。由目前掌握的资料可以知道,这批官员当中有很多人在光绪年间都曾于鄞县、慈黔、海宁、龙泉、德清一带先后为官他们中间的毕诒策、徐振翰、吴佑孙、王晓山、程熙增等人在任期间都十分重视文教;这次文庙重修时浙江一带的资金募化活动主要由王春明组织。综合分析这些信息,笔者认为这批同时段在同一区域为官的人彼此之间很可能存在一定的交集,甚至有着一些交往。由于其中有些人比较重视文教,也会对彼此有所影响。结合他们捐资重修南召文庙的行为是通过募化人王春明而间接实现的这一客观事实,可以看出王春明显然在浙江一带有着较高的声望,而且与其中某几位官员有着密切的交往。因此,在王春明的积极倡议和官员们的相互带动下,很快就得到了很多在浙官员的捐款。当然除了官员捐款之外,商人的捐资也是构成重修文庙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
受程颢出任晋城县令期间推行教化政策设立乡校的长期影响,在太行山区尚儒崇文思想日盛,民众务学蔚然成风。无论他们身份如何,读书进取这种追求已经潜移默化地融入他们的生活。民众这种尚儒崇文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们参与文庙创建与维修的积极性。在封建帝制时期,通过读书步入仕途的读书人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相对而言,拥有良好经济实力的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却并不是很高。所以商人阶层在积累了丰富的物资财富之后,更希望自己或者家庭成员能通过接受良好的文化教育而步入仕途,来赢得社会的认可,提升自身的社会地位。基于自身的需要和想要被社会主流群体认可的愿景,他们通过捐资参与文庙修建的方式,表达着该阶层想要改变自身社会地位的那种渴望。
从南召文庙重修时商铺捐资的情况来看,晋豫两地的商铺无疑贡献较大。其原因可能与地方商人进行的社会和商业活动有关。陵川县紧邻河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很多人入豫经商,他们在赚钱之后很乐意为家乡修庙这种公益善行尽一份微薄之力。至于本地商铺,他们更是乐而从之。
另外从参与南召文庙重修捐款的商铺所在区域与南召村地缘关系来看,这些商铺主要是分布在邻近陵川的外县商铺和位于本县区域内的当地商铺。这些商铺在地缘上靠近南召文庙,其所进行的商业活动也能够容易的辐射到该区域。因此,他们在文庙重修时进行捐款无异于在当地为自己和所从事的商业活动作了一个很好的宣传。而且他们出资捐助文庙的善举在一定程度上还会在当地官府与百姓中产生良好的影响,从而有助于提升、加强自己以及其所从事商业活动的知名度。同时,还会为他们进入该区域从事商业活动带来诸多便利,进而扩大其商业活动的范围,促使他们在商业活动中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对于只需要付出一小部分的捐款就有可能获得如此多的好处,他们有何理由不积极参与呢?由此可见,商人资助修庙的行为实在是一举双得的聪明做法。
从光绪十八年(1892)《重修文庙碑记》碑刻中提供的信息可以知道,承担文庙祭祀演出所用的专门性场所————戏楼,在此次重修过程中正式出现了。至此在文庙祭祀过程中献演戏曲的做法,在当地成为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而这种现象的存在却并没有受到官僚阶层的抵制和反对。所以也正是官方的这种宽松态度才在客观上给“文庙”剧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三、剧场的形成与祭祀演剧
戏楼是承担戏曲表演的专门性建筑,它的出现必定伴随着戏曲演出的进一步发展。南召文庙内戏楼、耳房、看楼这些功能性建筑的创修完成,标志着南召文庙专门性剧场的正式形成,从此在南召文庙演戏、观戏就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常态。由鸣凤张治昌”所撰清光绪十八年(1892)《重修文庙碑记》全文记载如下∶
尝谓庙宇之立,所以尊神圣,以维风化,贵整齐而不宜摧残也。即如南召村旧有文庙,创始未知,自有明以至国朝康熙年间,屡有重修碑记。及至今时,墙裂垣颓,不堪入目。光绪十四年春,乡老咸集,各输家资,公议重修。特是全腋之裘,非一孤所能集;万间之厦,非一木所能支。谨修募引,邀村中之远游四方者,向善捐资,由是兴工补葺。正殿与东西庑□仍其旧,独戏楼系改修,以及村东虫王、村南牛王、村北药王各庙补修。东西南北四路悉砌。至十八年秋间,工程告竣。谨择吉于十月十五、六、七三日,讽经献戏,鼓乐开光酬神,维社首索予为文以记。予观淫祀日盛,且有非所崇而崇之者。刘大圣人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先圣人而圣者,非圣人以明;后圣人而圣者,非圣人无以法。所谓仪范百王,师表万世者也。于以捐资重修,共劾盛事,使用春秋祈赛常新,宗社之规为公设,庶几有以慰圣灵欤。间镌于石,并旌善人,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碑文作者张治昌是一位接受过良好传统教育的邑廪生,自然十分清楚文庙祭祀的相关礼制。面对文庙祭祀在戏楼上进行戏曲演出这种并不符合相关礼制的现象,却在积极的为其存在找着合理的解释。在其为陵川南召文庙重修完成之后所作的碑文中以“尝谓庙宇之立,所以尊神圣,以维风化,贵整齐而不宜摧残也”的常理作为议论的开始,并以此理论为依据替民众重修南召文庙找着合乎礼制的解释。在他看来,对有些并未列入国家祀典范畴的民俗神进行的祭祀多为淫祀,与历来都受国家、官府重视的文庙重修、祭祀相比自然是不符合国家礼制。他认为在这样的庙宇重修之后都要鼓乐开光酬神,那么在文庙内对“仪范百王,师表万世”的孔子祭祀时除了常规的诵经之外,进行戏曲演出似乎也显得理所应当,所以文庙内建有戏楼也应该是合礼的。再加之戏曲演出在当地、当时已经非常盛行,百姓藉此既获教益,也得到愉悦。既然如此,在奉神、娱神时,民众就把“戏”作为贡品敬献给神灵。而这种祭祀神灵的礼仪之变,在乡间庙宇中实现起来要比其他地方容易的多。何况,在庙宇当中所演的许多戏曲剧目本身就是宣扬孔孟之道的。此次文庙重修完成以后,作者在撰写碑文时提到了“正殿与东西庑口仍其旧,独戏楼系改修”,从字面信息分析,推测在此次文庙重修之前该庙中就已经建有戏楼,可能当时初建戏楼之时其形制、规模并不完善,所以在此次重修之时,由于资金充裕,民众才进行了较大的改修,使其得以完善。因此,该庙戏楼之建当不晚于光绪十八年。对于文庙戏楼的存在,碑文的作者则认为这样做不仅可以使“春秋祈赛常新,宗社之规为公设”,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慰圣灵。纵观其为文庙重修所作的序文,无不透露着作者对文庙有戏楼,以及祭祀时演出戏曲这种特殊现象是符合礼制的认识。
除此之外,碑文还通过“至十八年秋间,工程告竣。谨择吉于十月十五、六、七三日,讽经献戏,鼓乐开光酬神”的记载直接给我们提供了两条关于献戏方面的信息∶其一、在文庙竣工之后献戏是重要的一项仪式;其二、明确了献戏的具体时间和天数。这与冯俊杰先生认为“神庙祭祀活动仪式中的最重要一项就是献戏。献戏一般是在春祈、秋报、神诞、开光、雩祭迎神,谢雨及神庙落成或大修竣工之时举行”的看法相吻合。可见在庙宇中献戏的本质大体一致,而此地"文庙"亦不例外。
除碑刻记载的相关信息外,戏楼上还留下了一些涉及演剧信息的舞台题记①。现将该舞台可辨识的题记整理胪列于下∶
一、司马庄 铡西宫 审诰命 忠保国二、山西陵川平城文工团
新夺印挂帅 司马庄 日月图□口驿 铡西宫 □□□收潼关□□□ 杨舍夺印 忠保国 闹花□ 小过山吵宫 拒□ 杀庙斩子 骂殿
三、龙回转□□风 天雷报 七下□□秋□ 巧□□ □金五
三龙殿□花楼 □□关 □金山 …月廿三日四、东城□老班
五、陵邑平城镇 光绪……
从这些剧目的名称上分析,它们多数为上党落子和上党梆子的传统剧目。而该“文庙”对于上演剧种和剧目倾向性的选择,应该与当地地域文化特征和民众喜好的影响有着紧密的关联。
按照礼乐传统,正规的文庙祭祀是由官府主持,在祭祀的过程中须用雅乐行礼,至于戏曲这种俗乐是不可能出现在这种祭祀场合的。但是南召文庙位于村落,受到官方意志的束缚相对较弱,其庙宇规制与祭祀方式自然与正规的文庙会有所不同。而这些差异的客观存在,其实是受官方对地方控制所存在的某些局限性,民众参与社会活动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等多重因素影响的。诚如车文明先生《20世纪戏曲文物的发现与曲学研究》书中所言∶“民间祭祀另有不同,历代王朝及其各级政府都没有也不可能给民间祭祀规定详细的礼仪制度,从而给民间祭祀的解释与行动留下了极大的自由度。”这里关于民间祭祀特殊性的客观认识,正好可以解释该区域文庙内修建戏楼以及祭祀时敬献戏曲做法的合理性。
综上所述,在晋东南多处乡村中出现的“文庙”并非传统定义所指的文庙。虽然这些位于村中的“文庙”与官方承认的正规文庙都是以孔子作为祭祀对象,但是在庙宇的规模、祭祀用乐等方面却迥然不同。作为一方文教中心的乡村文庙,按理在祭祀仪式中也应该遵循礼乐祭奠的基本规范,但事实却并非这样。在乡村文庙发展的过程中,其建筑形制与祭祀方式正悄然的发生着变化。文庙中逐渐出现了戏楼以及祭祀仪式中使用戏曲祭祀的特殊现象。而这种现象的客观存在,实际上是礼乐观念逐渐向民间普及过程中,文庙概念泛化之后才出现的。在帝制中国,政府不可能给这种泛化了的文庙祭祀也制定详细具体的礼仪制度。也是基于这种管控的局限性,才使乡村文庙建筑格局与祭祀形式能够按照民间的礼乐观念进行结构,从而促使具有民间特色的文庙剧场最终得以形成。
温馨说明:本平台目的在于集中传递全国各县、市考古成果,不作为任何商业目的,转载请注明出处。我们敬重和感谢原创作者,凡未注明作者姓名的文章,均因无法查获作者所致,敬请原作者谅解!如有涉及版权问题,敬请原作者或同行告知,我们将及时纠正删除。图文编辑校对过程中难免出现错误,敬请读者批评指正,我们将及时纠正修改。谢谢合作!